来源:游特 编辑:CC520WW 更新时间:2025-05-25 21:52:06
秋天的第一个包包图片大全:你的看法?最近也有各种各样模仿这个梗而被制作出来的图片,下面小编给大家分享秋天的第一个包包图片大全,接下来的内容大家可以看看。
>>>>小编推薦阅读(yuedu):秋天的第一个包包是什么梗
秋天的第一个包包图片大全今天小编给大家带来秋天的第一个包包图片大全最新内容,更多资讯相关内容,欢迎持续关注本站。
秋天的第一个包包图片大全内容及配图由入驻作者撰写或者入驻合作网站授权转载。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本站立场。秋天的第一个包包图片大全文章及其配图仅供学习分享之用,如有内容图片侵权或者其他问题,请联系本站作侵删。
上一篇: NBA巅峰对决球员怎样快速解锁
下一篇: 为什么我们买到的腰果一般都是没有壳的
相关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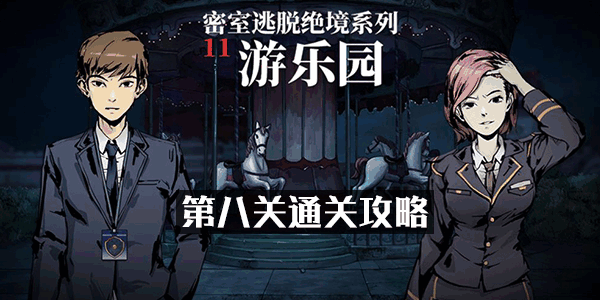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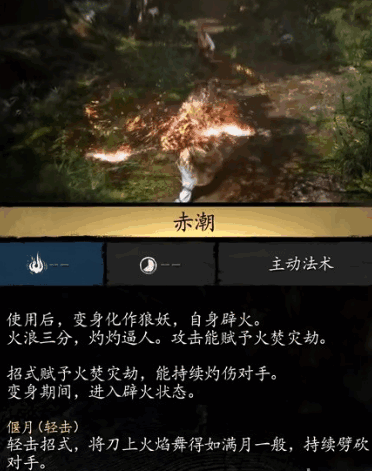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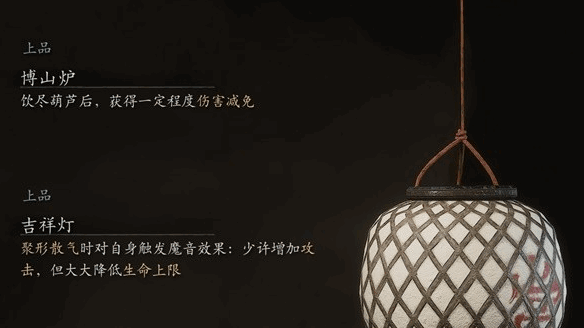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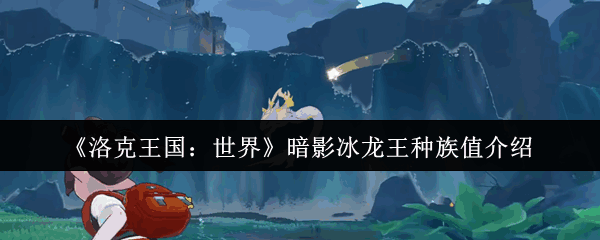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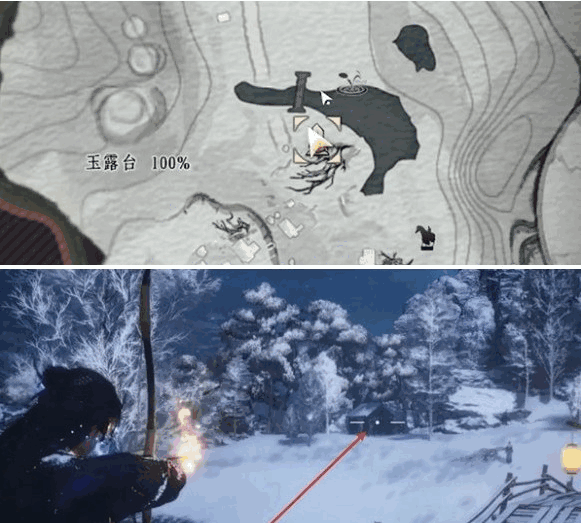


![[明日方舟]05月22日16:00闪断更新公告 - 明日方舟](https://img.yote5.com/uploads/take_images/2022zanwutupian.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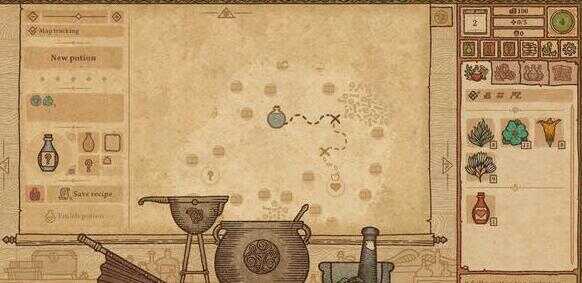
热门攻略
热门游戏
 预约
预约
模拟经营 48.73MB
 预约
预约
休闲益智 39.03M
 预约
预约
塔防策略 144.07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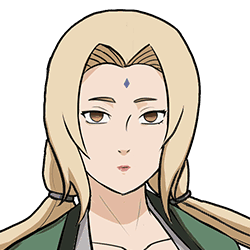 预约
预约
探索解密 18.5 MB
 预约
预约
角色扮演 84.55MB